【黃金神威│勇尾】We Kissed Under the Lake(HP PARO | 勇尾勇換梗挑戰)
- 參與了在噗浪上舉辦的「勇尾勇換梗挑戰」,抽的題目編號是306
- 收到的題目內容如下:
- 題目說是「兩種路線」,但就……我把兩題炒在一起了,希望題主別要介意
***
We Kissed Under the Lake
傻頭傻腦的新生一一戴過分類帽,然後在四院各自響起的歡呼與掌聲中,被迎進日後朝夕相對的學院中,與學長學姊以及未來的同學一一打過招呼。其後,校長和副校長分別站起來發表一番簡短的演說,以及一些望能減少意外發生的警告(葛萊芬多的學生在聽完便已在磨拳擦掌,準備親身去探探這些危險的虛實,像上年的他們不曾進過醫療室般),最後校長用銀叉敲了敲酒杯,宣布開學晚會正式開始。
各道佳餚美酒在餐桌上瞬間出現,看得一眾新生哇聲連連,但與台下興奮的學生相反,台上的一眾教授顯然已經司空見慣,見食物出來了,便從容地拿起酒杯互相祝一祝酒,然後拿起刀叉開餐。
任教魔藥學的尾形教授拿起酒杯,朝同事假笑了半秒,然後便把杯中物倒進嘴裏。用葡萄和各種香料釀製的美酒醇香撲鼻,令尾形每次經歷此等無聊的開學典禮時也稍微好過一點……他們應該早點派酒給他,就在這些新來的蠢蛋學生的鞋子踏上船板、不,應該從他們踏上火車那刻開始,霍格華茲就該派酒給他。
一想到他又要從「不要把刀子當玩具,否則我就把你的手指當水仙根一樣切碎研磨」開始重新教起,就覺得不如自己對著自己的腦袋來一發「空空遺忘」好了,這樣他會比較快樂一點。
尾形又嚥了口酒,然後把空酒杯放回桌上,待酒液自動添滿。他瞇著眼等待,而他的刀叉從沒被拿起過,碟中煎得極其漂亮的牛扒和在他手邊的鬆軟麵包、香甜濃湯、還有烤得表面金黃酥脆的南瓜派,全都被他無視掉了。
打了個呵欠,尾形拿起酒杯,正把嘴唇貼到杯沿時,忽覺身後一冷,然後一股冷風拂到他的側臉。尾形冷靜地喝了口酒,連眼睛都沒瞠大一點半星,鎮定得像早預計到這風會吹來。
只見他的身邊飛快湧來一陣灰霧,然後漸漸浮現出人的輪廓。一名身穿霍格華茲校服的年輕鬼魂笑瞇瞇的伏在他肩上,語調輕快地感嘆:「這南瓜派看起來十年如一日的美味,可真想念那甜而不膩的柔和味道。」
「勇作想吃就拿去。」,尾形咕噥著回答,酒精使他的咬字不太清晰,「我沒胃口。」
「兄長大人可真壞,明知道我什麼都拿不起來吧。」,勇作扁著嘴抱怨完後,便用力嘆了口氣,灰白的臉龐上的憂鬱活靈活現,「要是我能碰到事物的話,此刻定已緊緊抱著你了呀。」
說著,他伸出手,滿是眷戀的抱了下尾形。沒法成形的手穿過尾形的身體,尾形頓時感覺到自己的骨髓中像有一條蛇爬行而過,留下冰冷得噁心的詭異感覺;又像是在嚴寒之中掉進黑湖,那徹骨的寒意似乎連情感都能凍結。
尾形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全身的雞皮疙瘩都冒了出來,但蛇仍未離開他體內……畢竟世間再也沒有事物能阻止鬼魂愛著他深愛的人類。
他勾起兩邊嘴角,伸出青白的雙臂,穿過那縷灰白色的煙霧,從骨髓開始湧到心臟的寒意把他包圍,但他只是抱著他不朽的愛人,在新生詫異的紛紛議論聲與同事和舊生見怪不怪的目光中,側過頭親吻那道特別冰冷的空氣。
*
史萊哲林那位於湖底的交誼廳長期都濕濕冷冷的,哪怕柴火在壁爐中燒得劈劈啪啪,仍是驅不去這猶如黏在髮膚上的寒意。不知是哪人飼養的白蛇遊過走廊,一派悠然,濕滑的銀白色鱗片在大理石地板上磨擦,從主人房中偷溜出來的黑貓緊隨在後,黃銅色的眼睛饒有興味地盯著白蛇,上身壓得幾近貼到地上,蓄勢待發。
就在黑貓四肢躍起,正準備撲向白蛇之際,貓咪背後突然出現了一雙白晢的手,把牠抱了起來。
貓咪在人類的懷中不斷掙扎,四隻裹在白襪子裏的腳掌在空氣中划動,嘶啞地喵喵聲叫罵著,但人類只是拍了拍牠的小腦袋,然後低聲溫柔地呵斥要貓咪乖點。黑貓又張嘴叫了聲,像在回嘴,然後不情不願地讓人類把尊貴的牠的下頷按到肩上。
人類安置好貓咪後,左右張望了眼,然後微微啟唇,發出了嘶嘶的叫聲。
白蛇聞聲,從牆根探頭探腦的往人類方向靠,然後爬上人類伸出來的手,安安份份地捲著他的手腕休息。蛇吐了吐舌,嘶嘶聲的叫了兩聲,然後人類便開心地笑了起來。
「真的?那可真是個好消息。」,人類同樣嘶嘶聲的低喃,抱著一貓一蛇的他緩緩步向壁爐旁邊的沙發,然後把貓放到正坐在沙發上看書的人懷裏。
夜已經深了,交誼廳除了他們之外已沒有其他人在。
「請不要把貓抱過來,勇作閣下,她的毛會粘在我的黑袍上。」,說話者語氣冷淡,眼睛全然沒望過貓或人。指尖輕輕掀過米黃色的紙頁,課本經由他手所握,彷彿成了什麼上古經典。貓咪對著他咕嚕咕嚕的低聲嗚嗚,然後踡起身來睡在那人的膝上。
那人睨了放肆的貓一眼,然後把眼睛放回紙頁上,繡在校服上的銀線在爐火照耀下閃閃發亮。
「勇作閣下,請快把這頭胖貓拿走。」,他說。
被點名的人欣然聽命,連連噓了幾聲,把貓重新抱到懷裏。
「你打擾到兄長大人溫習了。」,勇作眼也不眨一下,便隨口誣衊了貓咪的罪行。
貓咪張嘴咬了主人的手指一下。
勇作吃痛得下意識把貓甩到地上,正合了牠的意,只見牠四蹄穩穩踩到地上,輕盈落地。牠回頭朝勇作瞇了眯眼,似乎在密謀要如何用牠又胖又毛的屁股捂到勇作窒息。
向來對自家的貓咪毫無辦法的勇作,只能甩了甩被咬痛的手指,連把貓抓起來打屁股都不願。什麼寵物都沒養的尾形,有些鄙夷地瞥了貓奴勇作一眼,而這副表情與他身上的綠銀配色校服甚為相襯,就是被鄰壁葛萊芬多稱之為「史萊哲林臉」的嘴臉。
要不是勇作能說得一口爬說語,任誰都認為他們院中出了個叛徒,還不是來自葛萊芬多,而是能令他們集體把白眼翻到後腦勺的赫夫帕夫。
尾形內心搖了搖頭,決定轉移話題,別再管勇作和他的蠢貓。
「準備成怎樣了?賽事。」,尾形又再翻了一頁,「想好要怎麼解決掉波巴洞和德姆蘭的選手了嗎?」
「噢,我有打聽到兩位選手的情報,我覺得這場比賽將會十分精彩。」,勇作規規矩矩地回答,像沒聽懂他哥指的解決是什麼,「我很期待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在霍格華茲未曾接觸的魔法……當然不包括會傷害他人的黑魔法,儘管我也想知道德姆蘭的學生會如何詮釋它們。」
勇作回答得就像接受報章訪問般(而實際上他日前接受記者訪問時,講的東西也是差不多),但尾形知道這番正直得像演戲般的言論是出自勇作的真心……就說了,他們的史萊哲林中出了個叛徒。
尾形聽罷,只能敷衍笑笑——他對這種答案毫無興趣。
*
那年的勇作是六年級,當了兩年級長,還是史萊哲林的魁地奇球隊隊長及追蹤手,人人都預計花澤家的嫡子將會在七年級時當上男生學生會主席,如同每一位傑出巫師的學生時代的軌跡一樣;而那年的尾形則已經七年級,正在準備超勞巫測,和他那偏科嚴重的成績單搏鬥中,想辦法維持魔藥學的卓越成績同時別掛掉其他科目。
那年亦是一度因死亡人數太多而停辦的「三巫鬥法大賽」復辦的一年。
飽受家族榮耀那套洗腦教育薰陶的花澤勇作,理所當然地報名了,然後火盃亦理所當然地選上這名優秀的年輕人。當寫上「花澤勇作」的羊皮紙條從紅焰中躥出來時,禮堂中的歡呼喧鬧得幾乎能讓麻瓜發現到霍格華茲所在地,人緣好得不可思議的優等生微笑著接受每一記向他投來的道賀與祝福,自信地走到三校校長的旁邊,與其他選手匯合。
那時尾形沉默地坐在下方的餐桌,安靜得與旁人相當格格不入。花澤勇作和尾形百之助擁有一半相同血緣這件事在霍格華茲並不是什麼秘密,畢竟兩人臉上那雙相似的眉眼,和現任正氣師總部部長如出一轍。尾形感覺到周遭朝他刺來的目光,大概是在說嫡子與私生子的雲泥之別,反正尾形已經無比適應,把它們視作魔法世界的空氣中的特有成份一部分。
校長拍了拍勇作的肩膀,無聲地為己校的驕傲打氣,勇作感激地笑了笑,然後嘴巴動了又動。尾形在台下理所當然地聽不到他講了什麼,但他腦海浮現出勇作那清亮的嗓音說著道謝的話。台上的世界金光閃閃,而尾形感覺自己和旁人之間隔了個湖:不是湖的兩邊,是他們在岸上,而他在黑壓壓的湖底。
感覺有些無聊的尾形拿起桌上無人問津的南瓜汁,自己給自己倒了一杯。又甜又黏的飲品讓他皺起雙眉,不理解像勇作這類巫師家庭出身的人,何以能夠把這玩意當水喝。
他突然想念起家中的麥茶。
這時,校長們都各自和自己親愛的選手打過氣了,其餘的教授和魔法部的官員一同站了起身,簇擁著三位天之驕子到旁邊的房間簡述賽程和注意事項。勇作忙於應對眾人的說話,眼睛都不知該望著哪一個說話者,畢竟他們總是同時說話……然後他的視線在亂轉間,不經意地越過層層肩膀,飄向台下史萊哲林長桌的一角。
兄長正拿著杯子輕抿,表情說不上有多高興……勇作心下扼腕對方並沒有察覺到自己的視線,抬起眼來與自己對望,儘管自己並無法衝下台擁著他,像德姆蘭的選手那樣張開手抱著自己的戀人,肆無忌憚地交換祝福的吻。
木門到了,魔法部的官員率先進入房,然後是三校的校長、霍格華茲的副校長、史萊哲林的院長,其後才是這場賽事的主角。年輕人一一進入房間,而花澤勇作走在最後,他在穿過門框前,依依不捨地再度回頭望了一眼……史萊哲林的學生已經從長桌間站了起來,正準備回到寢室。
他的兄長融進一大片一色一樣的黑袍中,在這一眼裏是找不到了。
勇作忍下這無法向任何人言明的寂寞。
那年,花澤勇作與尾形百之助已經交往了三年,但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他們兩人……於是乎,花澤勇作並未能在聖誕舞會中與對方共舞,還得忍受波巴洞的女選手邀請了尾形當舞伴,在開場舞時朝自己投來的挑釁目光……而他的兄長對此毫無反應,那女生需要一個舞伴來開場然後碰巧邀請了他,然後有人邀請他他便答應,只是這樣。
*
紫色霧氣氤氳在溫暖的池水上,鬆軟的泡泡浮在水面,一切一切都施了魔法,配上怡人的香氣使人放鬆。尾形扶著額頭上的白毛巾,瞇著眼睛打量牆上的畫作——依偎在他懷裏的勇作說那是他的第二項考驗。
第一項考驗是龍——不意外,反正他們不可能把催狂魔弄進比賽中;第二項的考驗是人魚——稍微讓人驚訝上一點點,但這無論怎麼想都要比龍來得安全,也不曉得那群老頭是怎麼想的。
「場地……」,在熱水中泡得頭昏腦脹的尾形忽地開口,「應該是在黑湖吧?」
「我也是如此猜測。」,勇作欣然同意——他當然欣然同意——補充道:「聽起來比上場考驗簡單,只是在人魚妨礙下,從黑湖湖底中尋物而已。」
第一場考驗在他的後背上留下了一道燒傷,護士的膏藥和治療咒語亦未能完全把傷疤祛除,仍需要多塗兩天藥膏,而勇作很高興他的兄長願意幫忙。粉紫色的池水被魔法隔開,沒能碰到勇作的傷口,同時亦隔開了尾形的指尖。
尾形就這麼隔著魔法氣泡描摹傷口,然後閉上眼低喃:「泡頭咒、變形咒、腮囊草……有本事被火盃選中的人,不至於想不出這些辦法來。那麼看來困難只在於我們親愛的神經病學校,到底在我們的交誼廳以及寢室上方養了什麼怪獸了。」
勇作聞聲輕笑,顯然明白兄長在不滿什麼:任誰突然發現自己的寢室窗外原來一直住著兇猛海怪心情都不會好,尤其在對比過其他院的交誼廳環境之後;史萊特林的象徵是蛇沒錯,但不是所有蛇院的學生都喜歡住在濕濕冷冷的地窖中,始終他們是人類,沒長鱗片。
佑大的級長浴室中只有他們,於是勇作也變得大膽起來。他在水下執起兄長的手,湊到唇邊,滿是依戀地呢喃:「不曉得人魚聚居在湖底何處,但要是就在交誼廳的窗外可見的範圍內,勇作便能在比賽中看到正埋首卷宗中的兄長……想到這裡,哪怕面對的是塞爾瑪湖怪也不足為懼。」
勇作曉得他的兄長並沒有去看他的比賽,但對此他並沒有任何不滿,因為他很清楚他的兄長是因為愛他才會在公開場合中與自己劃清界線……花澤這個姓氏帶給勇作的,除了榮耀和好處以外,還有與生俱來的種種責任和包袱。
聞言,尾形捧場地彎起唇角,朝勇作笑了笑,裝作對甜言蜜語相當受用的樣子,然後勇作便親在他彎彎的嘴角上。
*
尾形不清楚自己對勇作抱著的是什麼感情。
他曖昧地接受了勇作的示愛,用沉默回應對方那熾熱的情感,任由對方用擁抱用親吻用各種方式傾注他無比陌生的「愛」,默許對方在某個夜裏與自己在級長浴室中有過魚水之歡,但心底裏,尾形清楚自己並不愛勇作——應該說,他根本無法愛任何人。
愛和神明一樣虛無縹緲,哪怕是巫師也難以證得其存在。尾形在成長中、在學習中、在書卷中,理解到愛應有的姿態:感性的、無私的、偉大的、獻身的、命定的、溫柔的、美好的、救贖的、永無休止的……愈看愈費解,愈看愈像盲人摸象,愈看愈覺自己與這些形容詞的距離有如月亮和大海。
皎月看似每晚總會沉入海中,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月亮仍在萬尺高空之中,半點海水都沒沾到過。
勇作向他展示了兩種愛:一種是親情,他無比感激命運讓他擁有一名兄長,哪怕他們無法分享童年,又哪怕兩人的父親巴不得殺死尾形百之助;另一種是愛情,在尾形看來,就是當親情無法再滿足到生物想要接近另一個生物時,導致道德也無法限制他們軀體相疊時演變而成的情感姿態。
反正無論哪一個,尾形都沒有藍本可以參考,空洞的內在無法掏出什麼來回應對方,卻又不捨得推開這份從未有過的禮物,只得繼續沉默,用曖昧來助長對方的想像。如果你喜歡一棵樹的話,那麼對方就算只是被風吹得枝葉輕搖,於你眼中也是含羞答答。
尾形不知道勇作有否察覺到他所殘缺的機能,反正……就算察覺到了,如果花澤勇作仍然認為自己是「愛」著尾形百之助的話,他總得接受自己是愛著一個虛無黑洞的事實。如果他停止往深不見底的湖裏投石,那麼就連漣漪都會因此停下,兩人的關係也將迎來結局。
愛是感性的、無私的、偉大的、獻身的……永無休止的。
*
在第二考驗當日早上,勇作特意提早起床,在前往賽場前,施過幻身咒的勇作悄悄摸進七年級的寢室中,在一張張垂著綠色天鵝絨帷幕的古典四柱大床中,在窗邊那張找到他睡得正酣的愛人。
窗外粼粼的幽綠湖光映在尾形蒼白的臉上,白蛇盤在他的枕邊,察覺到勇作的接近而抬起蛇首,殷紅的舌頭吐了出來嘶了兩聲。勇作伸出無形的指頭,輕輕點了點白蛇的腦門,然後俯身在兄長緊閉的眼簾上輕吻。
仍然睏倦的尾形睜開眼,瞪著面前的空氣,腦袋仍有點昏沉的他得在勇作又再低頭親吻的他臉頰時,才意識到方才擦過他眼皮的是什麼。要是寢室內有人醒著的話,他們會看到相當奇怪的一幕:尾形伸出他青白色的雙臂,像在半空彈奏看不見的豎琴般移動,最後定格在一個別扭的姿勢,連後背都離開了床舖。
湖水擋住了陽光,相擁的兩人也不需要知道太陽是否已經東升,直至尾形推了推勇作,勇作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尾形倒回床上,繼續睡他的覺……他不相信什麼祝福,同時相信就算他不在場,勇作也會表現得很好。
卻沒想到竟然還有人來找他。
從假寢中睜開眼,尾形望向來人——來人跟他說明了第二場考驗的細節,請求他的協助:考驗是在黑湖湖底沒錯、是有人魚沒錯、是有水怪沒錯,但要尋的可不是什麼「物」,而是選手所愛之人。
尾形當時立即難以自制地笑了出聲,他就知道他們不可能成功瞞天過海到畢業,儘管來人並沒有說出他們是如何知道、也沒有說過誰會負責找出尾形。
*
其實被綁在湖底載浮載沉的時間,尾形什麼感覺都沒有,甚至連記憶都沒有,畢竟他被施了咒,睡得可沉了。他曉得選手收到的訊息是「只有一小時」,一小時之後人質便「有危險」,但實際上尾形認為這一切都只是在恐嚇,人質絕對會被保護得好好的,畢竟這三巫鬥法大賽能危及的性命只有自願跳上擂台的那三條;他相信當時限一過,素來與校方有所往來的人魚定會救回他們。
但顯然,他那無比天真的高潔弟弟並不這麼想。
尾形握著一杯溫熱的可可,坐在交誼廳爐火旁邊,碧綠的火炬照得周遭陰森森的,而事實上,霍格華茲本來就會鬧鬼。在湖中泡了數小時的他頭髮仍然濕漉漉的,護士檢查過他的狀況確認並無大礙後便泡了杯熱飲予他,叮嚀他最好乖乖喝光,然後同意了他回寢室的請求,但他卻在說過密令、通過石牆後,望到交誼廳上玻璃天花映著的幽綠湖水時,不自覺停下了腳步。
花澤勇作溺死了。
一介純血巫師,竟然溺死了,想到這裡尾形的嘴巴不禁漏出一連串破碎沙啞的低笑。據在岸上觀賽的人所說,勇作施展的泡頭咒相當完美;據教授所說,勇作的袍子口袋甚至還藏有備用方案腮囊草,只是不知為何,勇作並沒有使用。
尾形藉著爐火,他低頭看著指根與虎口間的瘀痕。他拒絕讓護士治療這道痕跡,尤其是從尾指下方開始並排的那四道。他放下杯子,摩挲著傷口,然後把左手疊上那些瘀痕,移動指頭直至和瘀青交疊……人魚拒絕讓選手救回「不屬於他的物品」,尾形知道這件事後便知道花澤勇作的死因。
左手牽著右手,尾形感覺自己仍在黑湖湖底未被救回,湖水灌滿了他的內臟,使它們變得無比沉重。「勇作閣下……」,尾形在聲音震動了空氣後,才發現自己開口喚了亡者的名字。
他微張著嘴,像被自己嚇了一跳般,然後他緊抿住唇,牙齒隔著皮肉啃咬唇瓣,呼吸急促而響亮。這突然的呼喚在安靜的交誼廳中無比突兀,使其他或在看書或在下棋的史萊哲林生都抬起了頭,望向正緊盯著爐火的尾形百之助。
細碎的議論不知是從哪個旁觀者的嘴巴開始,只知很快便像火燒燎原般擴散開去。高貴的蛇院生以為自己的聲量足夠自制,但顯然在數張嘴巴同時說話的時間,再小聲的耳語堆疊起來仍然相當喧鬧。
「勇作。」,尾形忽然又再喚道。這次他說得相當清楚,省卻了旁人猜測的功夫。
議論聲頓了頓,然後騷動得更為響亮,有些學生乾脆合上書來加入這場熱鬧。
柴薪在壁爐中啪的響了一聲,木頭裂開了。
緊接著,一縷灰濛的煙霧穿過牆壁,飛快吹到尾形面前,就停在他的鼻尖前不到一個指頭的距離。煙霧漸漸浮現出人的輪廓,半透明的校服的袍角在半空中翩翩飛舞。湖水在幽靈的身體上投下粼粼波光,幽綠的光照亮了他愛人模糊但溫柔的笑容。
尾形勾起兩邊嘴角,伸出他青白的雙臂,穿過這縷灰白色的煙霧,從骨髓開始湧到心臟的寒意把他包圍,但他只是抱著他不朽的愛人,在眾人詫異的紛紛議論聲中,閉上雙眼親吻面前這特別冰冷的空氣。
愛是永無休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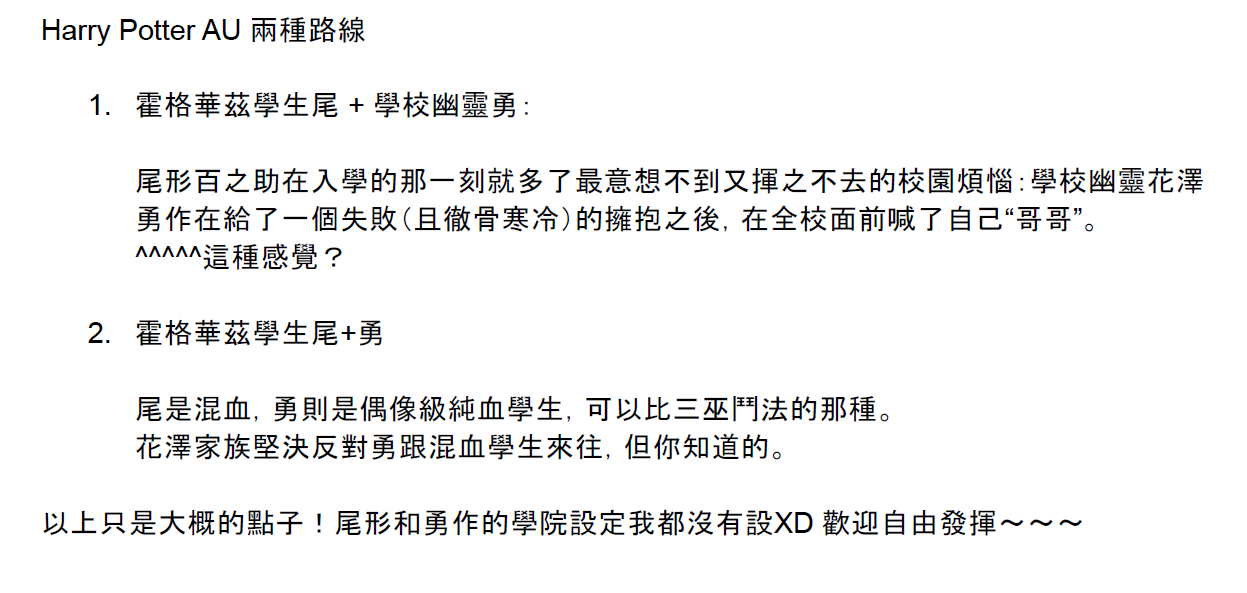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
有什麼想說的嗎?